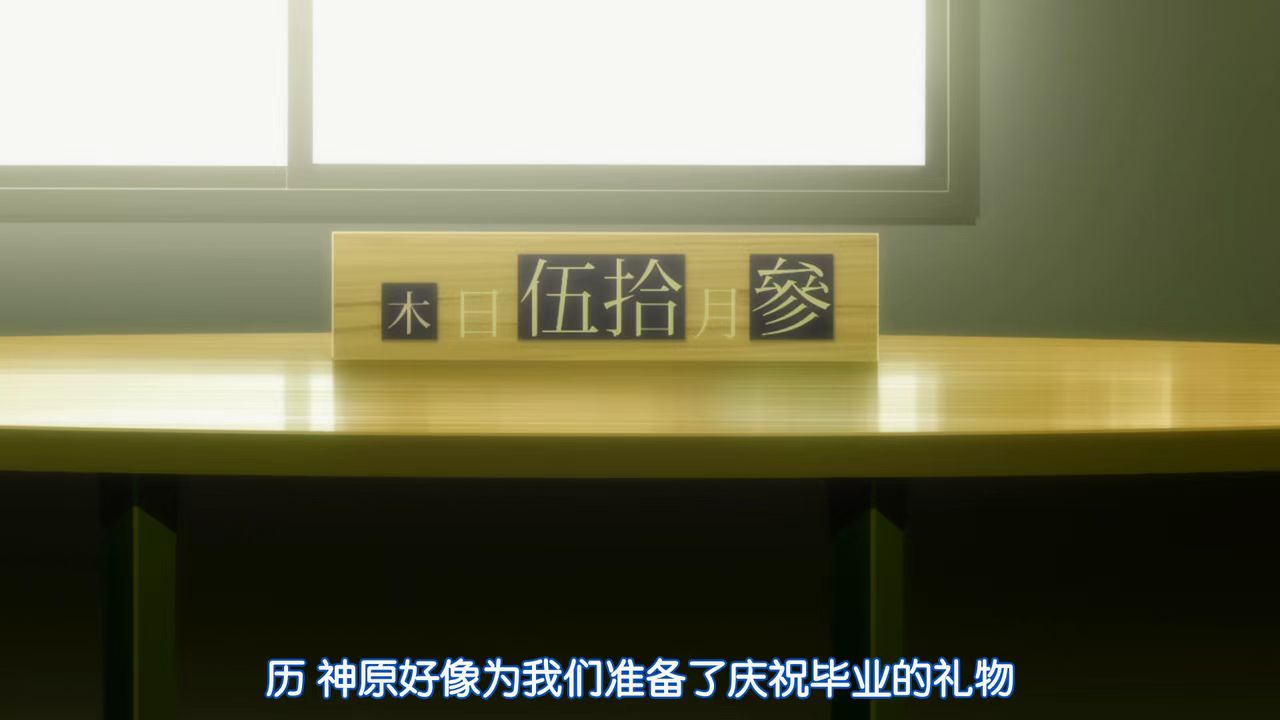《化物語》简评:
《偽物語》简评:
《〈物語〉シリーズ セカンドシーズン》简评:
《続・終物語》简评:
《〈物語〉シリーズ オフ&モンスターシーズン》简评:
前排提示:此文来源于作者本人昨日晚上睡不着时候的所思所想,距离作者本人看完物语系列已经隔了几月有余,如有纰漏望批评指正。
物语,monogatari,原本是志怪的文学体裁,后又引申为故事、传记。而在本作中又重新回归的本源:对于怪异事物的故事。
一、何为怪异
怪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异常之物”的含义,平凡而又不变的日常生活即为“常”,那“异常”自然也就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变数。
其中的人物大多都处于青春期,或者说快速成长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里,经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区别。对主人公或是处在这一时期的人来说,与以往相对比,这很难不说是身体上出现了“怪异”,同时心智的开化驱动了对现世未知的探索。在认识到周遭世界似乎并不与自己所以为的原本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喝求知欲,而恰好这份旺盛的求知欲所带领主角们探索的那份所谓未知也会成为怪异的一部分。所谓“怪异”表面看是服务于物语里故事的唬人怪兽,实则是正处于青春巨变的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外化,是一种更为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一种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无论是螃蟹、蜗牛、蛇还是猫,它们都是名为“怪异”的载体,承载的所有人类在面临成长时的各种负面情绪。作为经历这一切的主体,就是人本身。运用怪异,将异变搬到台前,把存在于同一个个体的相反二者,强制剥离出来。强制引导在观众面前,这不仅仅是图方便的演出手法;不仅是通过制造反派来促进故事的进展,更是一种强调的表现手法,逼迫故事主角推心置腹地去解决成长所遇到的问题。相当于一种请君入瓮。在这里,“我们”和依附于自身的“怪异”就是主角。
二、叙事逻辑
于是乎我们就可以简单一窥他的叙事逻辑。
只要看过的观众很简单就可以发现,一个单元的故事基本可以概括为:
➡遇到怪异(影响他人的结果)
➡找到解决怪异的方法(寻因)
➡解决(与处于成长路上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自己的和解)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是否所有的故事都是依照这个模板叙事的,在这里不做详细解读。
这样的叙事逻辑本质上是和各位的成长路径相似,其故事本质上只是“物语化”的日常,套了一层妖魔鬼怪的皮,讲日常生活的实。
三、大体演出
闪回的画面,快闪到让人看不清的文字和纯色画面,独到的场景设计和符号化的表达是物语系列的标志。物语是一部志怪小说,其故事已是以一种被讲述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并不是类似jrpg或打怪闯关。由于其主线的根基是主线角色的成长,因此必须添加大段的心理和人物对话才能推动故事的进行,这样也就不得不要求创作者要解决长篇大论带来的无趣和枯燥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在后面的故事常有发生)
新房昭之以一种“让人物动起来”的演出方针来指导物语片场的演出设计,在人物对话中添加不想干的动作,场景的变化。借助外物和动作的表现力比单单言语的表现力不可谓不是更上一层楼,新房昭之就这样巧妙地解决了长篇大论带来的最大问题,同时在在过程中添加闪回更是这种理念的深化。枯燥的根本原因是“冲击”太小,于是加上闪回和文字构图这种既能提升画面信息量,激发观众想象力又能带来视觉冲击的做法就让物语变得更加有趣。
动画的原教旨是有趣,有趣的根本在于不平常,在对话中加入看似不相干的动作和添加闪回都加剧了这种“不平常”,这样的演出在故事推进方面也有益处。在诉说故事的走向之时新房昭之往往通过“全-中-近”三段的方式来表现人物述说时的动态同时每一个镜头在辅以不平常的角度,能更好地博人眼球。这是一种极好的视线引导,同时也是动画添加有趣程度的一种小手段(可惜这在之后的物语基本销声匿迹)。
但这种方式也对创作者的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主角要动,如何动?要看,如何看?要说,如何说?以及如何用平常的事物来类比人物的心境(比如:爆米花-内心躁动)用怎么样浅显而不失风采的符号来表达,这也就成为后续物语的主要问题。一般人是把握不好这样的度的往往只会东施效颦。
演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场景设计。比如阿良良木加是美术馆,黑仪的家则是舞台。天花板还常有聚光灯的参与。同时在人物对话展开之际还会刻意地把场景扁平化。往往会用很小的透视再辅以前文所说的三段演出公式,做出一种“物语味”。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这是制作组有意的营造一种“话剧感”或者说“戏剧感”,就像押井守的「御先祖大人万万岁」一样,这种“戏剧感”无疑是很不真实的。这种不真实感则是暗示观众这根本不是平常的世界。
不以观众带入为目的的表现故事方式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奇怪,但恰似这种戏剧感能更好地告诉观众:我们之所处,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小镇,而是一个“志怪者也”的幻想乡。意在提示观众运用象征主义的解读手法来参透本作的奥秘,而这种考量也和本作的故事表达及内核相对应。
当然这仅仅是大体的演出方针,具体的拉片还请移步其他日志...

来自:Bangumi